黃亮斌《大靈山探源》
暖暖的陽光灑滿大地,這是一年中最宜人的秋季。不久前我剛剛到訪過澧水尾閭——津市小渡口,這次又到武陵山脈深處的龍山縣做生態文學交流。探尋湘西之巔、澧水之源的大靈山,我自是十分向往,期冀以此來滿足自己探知一整條河流的好奇心。
澧水有北、中、南三源,北源在桑植縣西北八大公山,中源在龍山縣大安鄉的大靈山,南源則在永順縣龍家寨。南源和中源先在桑植縣兩河口匯合,繼而與北源在桑植縣小茅巖匯合后東流。澧水的主源,過去認為是北源,十多年前則認為是中源,因此我對大靈山的探訪便有了某種正本清源的意味。盡管我知道不捐細流方成江海的道理,但內心中尊高、尊遠、尊奇的心理總是時時泛起。更何況大靈山不僅是澧水的源頭,與它緊挨著的七姊妹山還是沅水最長支流——酉水的源頭。對大靈山的一次探訪,差不多走進湖南四大河流中兩條河的源頭,這種“一山兩河”的獲得感讓我興奮不已!

大靈山主峰1737米,抵達大靈山的旅程十分平順,出龍山縣城往西北一個小時的車程便到了大安鄉翻身村一處露營地,營地海拔1400米以上,離大靈山主峰僅有咫尺。大安鄉由原來的大安鄉、烏鴉河鄉兩個鄉合并而成,但誰合并誰其實很有講究。烏鴉河鄉原本是富庶繁榮、商賈云集之地,政府所在地——地龍堰,更是傳頌著一則動人的神話:那一年,嫦娥廣寒宮桂花樹上的一只神鴉因思念凡塵,偷偷下凡,變成漂亮的女子并與當地一位后生結婚。嫦娥發現后派一條五爪金龍前來捉拿,龍鴉大戰3天3夜。神鴉精疲力竭而亡,血化為一條河,兩只眼睛化為兩個潭,一個叫龍堰,一個叫西堰。這里的人們為了紀念這只神鴉,便把村莊叫作烏鴉河。20年前一些電力資本在這里跑馬圈地,但澧水發脈之處沒有形成浩蕩江流。大功率發電需要的勢能尚未形成,人們便攔河筑壩,在澧水上游的內河口建成第一個引水式水電站。原本從高山峻嶺自然流淌的山水,經打通的兩個小山頭引入內河口電站,就有了一萬千瓦水力發電所需要的水量和勢能。但自此以后,缺乏山水滋潤和養育的烏鴉河,慢慢露出日益見底的河床,烏鴉河鄉也因供水不足,在一波撤鄉并鎮的熱潮中并入大安鄉。地處大靈山主峰下首的大安鄉政府,水量的豐沛經受了2022年大旱的考驗。當人畜飲水困難的幾個村子需要政府組織水罐車送水時,鄉政府所在地采取限時供水的辦法,基本上能夠保障集鎮居民用水。
在露營基地用過中餐,便想著早點向大靈山主峰進發。我聽過一位湘西女作家徒步2個小時、歷經艱難險阻方才登頂的講述,心里也就早早做好走出一身老汗的準備。但陪同的老潘說正在修的一條公路可走,便隨著他上了車,原來是一條2個月前才開工的森林防火應急道路。近年來,大靈山大力推進長江生態林保護、天然林保護、公益林保護等森林建設工程,森林覆蓋率已超過70%。按照森林火災高風險區安全保障的要求,應該建設森林防火應急道路,這樣便有了第二條公路建設項目。4年前一家大型電力公司在這里建設風電場,山上有了第一條公路,從此大靈山孤遠壅蔽的交通狀況得到徹底改觀。便利的交通也把更多的游人導引上來,源頭芳姿也從深閨走進世人眼中,這自然是很多人都欣然樂見的。但轉念一想,澧水與三峽一帶同屬長江流域暴雨集中區,又地處武陵山區走向洞庭湖的過渡帶上,總長400公里水路有著1400米的河流落差。湖南四水中最短的澧水卻是最任性、狂野的河流,多次洞庭湖特大洪災,都有澧水作祟的影子。因此,我又希望人們進入源頭的步伐更慢一點、遲一點,讓最原始的生態更好地涵養這里的水源。正這么想著,車行至新修公路的一處盡頭。老潘告訴我,下車后步行一刻鐘就可以登上大靈山主峰。沿著一段長滿青苔的水泥路往上走去,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大片有著闊大葉子的厚樸林。厚樸是大安鄉三大藥材之一,另外兩種藥材分別是杜仲和黃柏。然而,大安鄉最主要的收入還是上萬畝上等煙葉。煙葉與藥材,既耐旱也耐熱。大自然的饋贈使得這里的人們豐衣足食,大安鄉因此成為龍山縣生活最富裕、民風最淳樸的鄉鎮之一。離開厚樸林,我們便被一株濃蔭覆蓋的衛矛樹吸引。如今這種被廣泛用于城市庭院的低矮灌木,正高大挺拔地長在這里,足顯大山滋養的豐厚。老潘還告訴我,樹林深處還有一株湘西最大的珙桐樹,當年他親手給這棵樹王做了標識。

我還在幻想著大山的鵝黃嫩綠、澗底谷音,不覺幾步之間已到山頂。雖汗不流、氣不喘地輕易登頂,但這種唾手得來的美景,似乎又缺乏艱辛跋涉方能登頂的那種過程之美。山頂置一亭,老潘一邊贊嘆如今交通之便利,一邊感嘆這亭子建設“生不逢時”。建亭時每一塊磚頭和瓦片,都是靠著騾子馱上來的,非常耗時費力。要是現在靠著車輛運輸,費用大概可以省下一半。我站在這湘西之巔,恣意地把萬山看遍。但見白云之下,天廣地闊,群山巍巍,層林莽莽,氣象萬千。朝北看是同屬武陵山脈的湖北宣恩縣七姊妹山景區;朝東看是桑植縣境內的八大公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,更遠處便是開國元帥賀龍的故鄉——洪家關;朝南看則是烏龍山國家地質公園,那里曾經演繹過湘西剿匪的傳奇;朝西看正是澧水和酉水共同的源頭,澧水朝東,酉水向南,兩條河流在山林石罅間一路奔流,一路跳躍,一路歡歌。
前年長江流域大旱后,我先是沿著長江干流從干涸洞庭湖走到可以草原跑馬的鄱陽湖,后又從重慶朝天門走到巫山縣大寧河,試圖探究母親河的極端干旱究竟是偶發的自然災害,還是趨勢性環境事件。在這種對“源頭活水”尋尋覓覓的行走中,我看到在科技的加持下,人們正以更深更重的生態腳印,向著大自然更深更遠處延伸與挺進。
作者簡介:
黃亮斌,資深環保人,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湖南省作家協會生態文學分會代理主席。已出版散文集《圭塘河岸》、報告文學《湘江向北》、名物學專著《以鳥獸蟲魚之名走進詩經中的動物世界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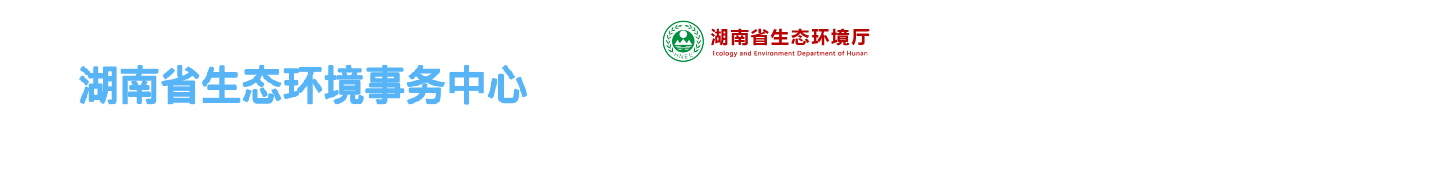


 湘公網安備 43011102000964號
湘公網安備 43011102000964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