鄧水平《有一種思念是故鄉》
闊別故鄉生活已有33年,母親健在時,每周末會抽空去看看,但,很少會住宿。或許是衛生,生活習慣的改變,或許是工作,應酬的緣故,又或許是語言,文化認同等因素,總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借口與理由。去年,母親走了,思鄉之情卻愈發強烈,有時還有想在故鄉建房生活的沖動。
我的故鄉坐落在山水之間,遠離喧囂的都市,猶如世外桃源。村莊依山而建,前有太子山,后有背脊嶺。在我的記憶里,太子山是村里土葬老人的地方,歸宿著無數的祖先,平日里冷冷清清,寂寥而肅然。一到清明,這里熱鬧非凡,鞭炮聲,花炮聲,呼喊聲是此起彼伏,清明節一過,又恢復往日的寧靜。太子山也有部分旱地,基本是自家有需求膽子又較大的人開墾出來,種點蘿卜、辣椒、紅薯、白菜等蔬菜。我父親退休后回到故鄉,不信邪,不怕鬼,就在此開荒十幾畝旱地,種些花生、玉米、茄子、辣椒等農作物。那些年,我們姊妹四個家庭的蔬菜與農作物基本來源于此,每到周末,父母都會在北村口翹首相盼。父親離世后,母親還種了幾年,最近幾年,因母親年事已高,姊妹們不讓她再勞作,才把旱地交付我二哥。二哥經營這幾年,就不再種蔬菜和農作物,聽說種了尾參,年成好的時候,尾參護養得好,一畝尾參能賣不少錢。
背脊嶺是村里的后龍山,也是村里的神山,一般是不讓人在山上動土建房。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,村里有一個堂叔從鐵路部門退休,回到家鄉開墾后龍山種植果樹,本意是想帶動村民發家致富,但事與愿違。由于山體植被損壞,不到一年,村里的三口井都不再清澈,一到雨季,井水就更加渾濁不堪,村民從此再也未飲上甘甜的山泉水,我的故鄉從此成了缺水的村莊。沒過幾年,堂叔就在村里人的責備聲中攜妻離開了故鄉,我再也未曾謀面這位堂叔。有老人說,是堂叔觸怒了后龍山的山神,山神便以此懲罰村里人。這種說法,我自然是不信的,但還是覺得十分遺憾!
故鄉靠北村口有幾十棵上百年的松柏,樹齡最長的有460多年,這是故鄉900多年來形成的風景林,見證了幾百年的風霜雨雪、春華秋實。北村口是村里的風口,風大,樹林茂密,夏天涼爽,是村民納涼的好去處,這里賜予我兒時的許多歡愉。曾記得,經常和伙伴在這里“打哇哇”,小時候,沒有電視,沒有手機,放學后就會邀上三五個伙伴,到田里先取土,然后到風景林的石板上把土和泥好,制成碗狀,對著泥碗喊幾聲“哇~啊~”,再舉過頭頂,向石板上一撲,“泥碗”中間隨著一聲刺耳的響聲泥巴飛迸,爆出一個大洞,誰的“泥碗”洞大,響聲最響就是贏家。反反復復,樂此不疲地玩著,有時過了飯點,大人來喊吃飯才肯作罷。
村莊南村口有一片空地,空地上原有一庵,因位于村口的南角,因此那一片就叫庵子角。庵子角,據碑載:庵原叫鳳鳴庵,始建于萬歷七年,后崇禎甲戌年,在庵里塑觀世音菩薩,十八羅漢等神像,后在康熙甲戌年重新整裝,并命名觀音閣;在通往庵子角的小溪上建兩座橋,一座建于大明嘉靖十年,稱來鳳橋;另一座重建于嘉靖四年,命名鎮溪橋。據村里上了年紀的老人講,這里曾經香火很旺,特別是初一、十五及傳統佳節,十里八鄉的村民都會來此朝拜祈禱,尤其是祈子嗣求富貴為多。受文革影響,那座庵,那些古跡現早已不在,留給后人的只是一份記憶。現如今,那片空地已成一片林地,郁郁蔥蔥,特別是一種叫“千年矮”的樹木保存完好,以它頑強的生命力見證著故鄉,見證著庵子角的滄桑巨變。村前有一條小溪沿村邊向南而流,與另一條穿過村莊的小溪出村后相匯,或許故鄉稱下溪村應該與村前的小溪有一定的淵源。村的周邊基本是耕地,村口小溪兩岸都是桂花樹。每到收割季節,稻田里金燦燦,村前村后綠油油,桂花飄香,三五成群的燕子起起落落,藍藍的天空彌漫著清新的鄉土味,沁人心脾,再有幾個老人在村口悠哉樂哉的吸著自制的喇叭煙,聊著天……真是一幅古樸優雅的山水田園畫。我曾記得,一到夏天,因放學早,兒時伙伴們就會相約先到小溪邊的田間地頭扯豬草,扯完豬草后,有時會找個空地,把自己扯的豬草,放在三角叉下,三至五米遠,看誰能把三角叉打倒,打倒三角叉者豬草就歸誰;有時天氣太熱,也會把豬草籃放在溪邊,脫光衣服到小溪深處去游泳,那個時候的家長不會像現在這么管得緊,看到了也只會說一句:“你個死崽注意安全啊。”也就是那時,我不僅學會了狗刨式游泳,還學會了抓蟹、抓魚。到部隊后,也就不再像有些北方的戰友那般怕水。
月是故鄉明,水是故鄉甜,人是故鄉親。
有故鄉的人是幸運的,更是幸福的,因為故鄉養育游子,游子賦力故鄉,彼此成就,源遠流長。故鄉是用來離開的,我曾是故鄉的一粒塵埃,飄忽不定;故鄉是用來擔當作為的,我也曾因工作上進,獲得組織認可立功受獎;故鄉是用來激發奮斗意志的,在面對艱難困苦時,讓我從未退縮;故鄉更是用來思念的,在孤獨無助時,在傳統佳節時,倍加思念。
有一種積淀,有一種依靠,有一種感恩,有一種期待,有一種思念……是故鄉!
作者簡介:鄧水平,供職于湖南省郴州生態環境監測中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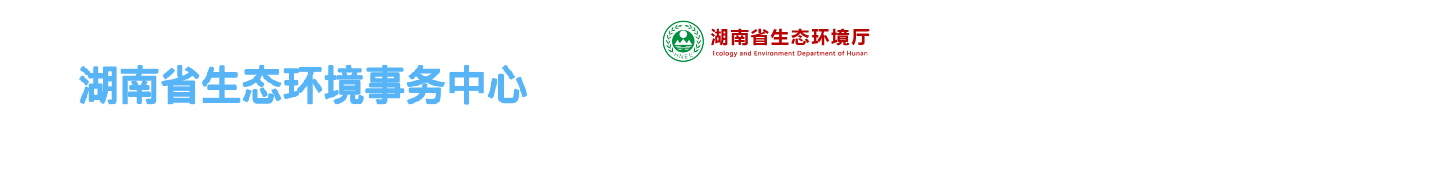


 湘公網安備 43011102000964號
湘公網安備 43011102000964號